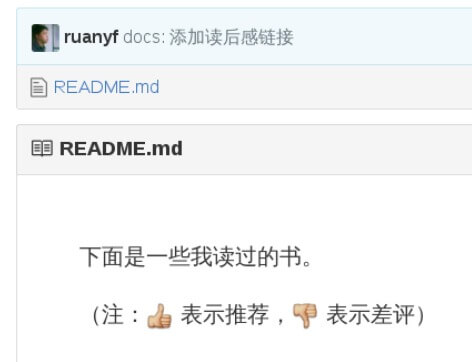上週,我整理了過去幾年讀過的書,做了一份書單。
然後,發現自己好久沒寫讀後感了,上一篇還是兩年多前的《做學問的八個境界》。過去幾年,這個部落格已經偏向純技術了。雖然今後也會如此,但我覺得,讀後感還是應該堅持寫下去。
今天就介紹,我最近讀完的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說《青春》。

這本書是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南非作家庫切的"自傳體"小說。

它講述了一個名叫約翰的年輕人,大學畢業後,為了逃避南非的種族對立,獨自一人來到倫敦追求理想的故事。小說內容跟庫切的個人經歷完全吻合,但又有藝術加工和虛構的部分。讀來讓人覺得很真實,但又像在聽故事。
整本書都是約翰的內心獨白,沒有貫穿始終的情節。他講述生活中的各種遭遇,然後傾述自己的內心感覺。自己提問,自己回答。如果你喜歡曲折的情節,大概不會喜歡這本書。但是,如果你對探索精神世界有興趣,尤其是有過精神苦悶,那麼你會愛不釋手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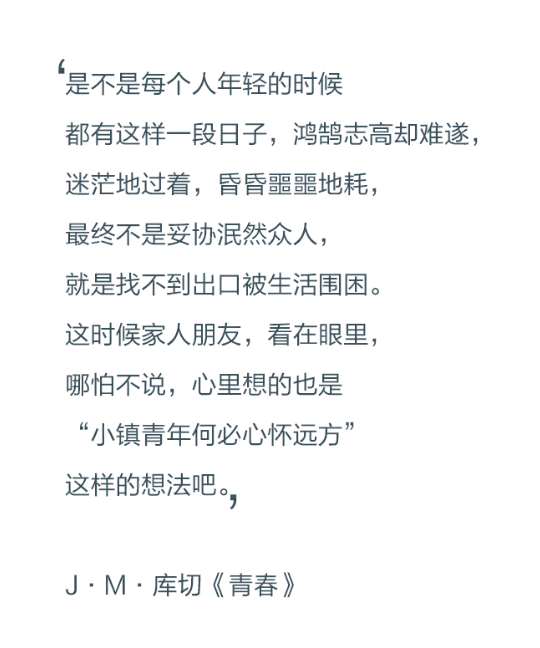
約翰愛好文學,希望成為一個詩人或者藝術家。但是,他來到倫敦後,只找到一份IBM公司程式設計師的工作。
面試官想知道的第一件事,是他是否永遠離開南非了。
是的,他答道。
為什麼?面試官問。
"因為那個國家要發生革命了。"他回答說。
約翰很快發現,IBM公司的這份工作,根本就在扼殺自己的生命力。
"隨著時間一週一週地過去,他發現自己越來越痛苦。驚恐會向他襲來,他費力地將其擊退。在辦公室裡,他感到自己的靈魂在受到襲擊。辦公樓是一個毫無特色的玻璃水泥大廈,似乎散發出一種氣體,無色、無味,一直鑽進他的血液,使他麻木。他敢發誓,IBM在殺死他,把他變成一具殭屍。"
他在倫敦的生活也很糟糕,因為沒錢。
"他在倫敦北部牌樓路附近的一所房子裡,獨自租一個房間住。房間在三樓,能夠看見水庫,有個煤氣取暖器和小凹室,裡面有煤氣爐灶和放食物及碗碟等用品的架子。在一個角落裡是煤氣表,你放進去一個先令,得到價值一先令的煤氣供應。"
"他一早就離家,回來得很晚,很少看見其他的房客。他在書店、美術館、博物館、電影院裡度過星期六。星期日他在房間裡看《觀察家報》,然後出去看個電影,或到荒野去散步。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是最難熬的。那時,寂寞感會傳遍全身,和倫敦的陰沉多雨的灰色天氣、冰冷鐵硬的人行道合在一起。"
在冰冷的現實面前,他原來的人生計劃很快就破滅了。
"原本,他來英國時,心底裡計劃就是找個工作,攢點錢。當他有了足夠的錢就放棄工作,獻身於寫作。積蓄的錢花完了就去找個新工作,如此等等。"
"很快他就發現,這個計劃是多麼幼稚。他在IBM的稅前工資是每月六十英鎊,他最多能夠存下十英鎊。一年的勞動能夠為他掙得兩個月的自由,而這其中的許多時間還得花費在尋找下一個工作上。南非給他的獎學金只夠勉強交學費。"
"而且他還得知,他不能夠隨意自由地更換僱主。管理居住在英國的外國人的新條例規定,每一次改變就業都需得到內政部的批准。禁止閒散無業,如果他在IBM辭了職,必須很快找到別的工作,要不就必須離開英國。"
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悶。
"他覺得自己像個狄更斯小說裡厭倦無聊的小職員,成天坐在凳子上抄寫發黴了的檔案。惟一打破一天的單調沉悶的是十一點和三點半。這時,送茶的女士推著小車,在每個人面前啪地放下一杯英國濃茶("給你,親愛的")。"
"他為什麼會在這個巨大而冷漠的城市裡,在這裡僅僅為了能活下去,就意味著需要永遠死命拼搏、力求不要倒下?"
"他暗自想到,我們要為了精神生活而獻身嗎?我以及在大英博物館深處的這些孤獨的流浪者,有一天我們會得到報答嗎?我們的孤獨感會消失嗎,還是說精神生活就是它本身的報答?"
當時正是越南戰爭時期,他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。
"他給中國駐倫敦的大使館寫了一封信。既然他猜想中國不需要計算機,就沒有提計算機程式設計的事情。他說自己準備到中國去教英語,作為對世界鬥爭的一個貢獻。工資多少對他並不重要。"
"他把信寄了出去,等待答覆。與此同時,他買了《自學漢語》,開始學習漢語那陌生的咬緊牙齒的發音。"
"一天又一天過去了,中國人沒有答覆。英國特工截下了他的信銷燬了嗎?他們截下並銷燬所有寄往中國大使館的信件嗎?如果這樣,允許中國人在倫敦設立大使館有什麼意義呢?或者是,在截下了他的件以後,英國特工有沒有把他的信轉到內政部,並附上一張條子,說在XX計算機公司服務的那個南非人暴露出了他具有的共產黨傾向?他會不會因為政治丟掉工作,被驅逐出英國?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,他不打算對此提出質疑。這將是命運的聲音;他準備接受命運的決定。"
他對自己產生了巨大的懷疑,自問追求的東西是不是錯了,要不要放棄理想。
"這是一個他可以逃避的世界----現在逃還不晚,或者與之和解,和他看到的周圍的一個個年輕人那樣,滿足於婚姻、住宅和汽車,滿足於生活能夠實際提供的,把精力放進工作之中。他懊惱地看到,講求實際的原則多麼奏效。"
他與不同的女孩交往,頻繁地發生性關係,為了不讓自己被苦悶淹沒。但是,還是無法擺脫深入骨髓的孤獨感,以及對未來的無力和迷惘。
"在泰特畫廊,他和一個他以為是來旅遊的女孩聊了起來。她相貌平平,戴副眼鏡,身體結實,是他不感興趣的那種女孩,但很可能他自己就屬於那種人。她告訴他她叫阿斯特麗德,來自奧地利----是克拉根福,不是維也納。"
"原來阿斯特麗德不是旅遊者,而是個以幹家務換取在主人家吃住的女孩。第二天,他請她出去看電影。他們的趣味很不相同,這點他立刻就看出來了。然而當她邀請他一起回到她工作的人家去的時候,他沒有拒絕。他看了一眼她的房間:一間閣樓,藍色方塊布窗簾和顏色相配的床罩,枕頭上靠著一隻玩具熊。"
"後來,他再一次邀請阿斯特麗德出來。沒有什麼特別的原閔,他說服她和他一起回到他的住處。她還不到十八歲,還有點胖乎乎的娃娃樣。他從來沒有和這麼年輕的人在一起過----其實她還是個孩子。他給她脫衣服的時候,她的皮膚摸上去冷而黏溼。他已經知道自己犯了個錯誤。他沒有性慾。至於阿斯特麗德,雖然通常女人和她們的性需求對他是個謎,他確知她也沒有感到有性慾。但是他們兩個已經走得太近,欲罷不能,因此就幹到底了。"
"在此後的幾個星期中,他們又一起過了幾個晚上,但是時間永遠是個問題。阿斯特麗德只有在主人家的小孩上床睡覺後才能出來,在返回肯辛頓的末班火車之前,他們最多能有匆忙的一個小時,有次,她大起膽子和他過了一整夜。他假裝喜歡有她在,但事實上他不喜歡。他單獨睡覺睡得好些,有人和他同床。他整夜緊張地直挺挺地躺在那裡,醒來時筋疲力盡。"
"有好幾個星期,他沒有和阿斯特麗德聯絡了,她來電話了。她在英國的時間巳經結束,要回奧地利的家裡去了。"我猜我不會再見到你了,"她說,"所以打電話和你告別。"
"她盡力就事論事地說話,但是他能夠聽出她含淚的聲音。他愧疚地建議見一面。他們一起喝咖啡;她和他一起回到他的房間裡過了一夜(她稱之為"我們最後的一夜"),緊緊依偎著他,柔聲哭泣。第二天一早(是個星期日),他聽見她悄悄下床,躡手躡腳地走進樓梯平臺處的衛生間去穿衣服。她回來的時候他假裝睡著了。他知道,他只要稍作暗示,她就會留下來。如果在對她表示出關心之前他想先做別的事情,比方看報紙,她就會安靜地坐在角落裡等著。在克拉根福,女孩子在行為舉止上似乎受到的就是這樣的教育:不提出要求,等待著男人準備好的時候,然後為他服務。"
"他很想對阿斯特麗德好一些,她是這徉年輕,在這個大城市裡是這樣孤單。他很想給她擦乾眼淚,逗她笑;他很想對她證明,他的心腸不像看上去那麼冷酷,他能夠用自己的樂意回應她的樂意,樂意像她希望被摟抱的那樣摟抱她,傾聽她講述的關於她在老家的母親和兄弟們的故事。但是他必須小心謹慎。過多的熱情她就可能把票退掉,留在倫敦,搬來和他同住。兩個失敗者在彼此的懷抱中躲避,彼此安慰:這個情景太令人羞辱了。要是這樣,他和阿斯特麗徳還不如結婚, 然後像病人般互相照顧,度過一生。因此他沒有作出暗示,而是躺在那兒緊閉著眼睛,直到聽見樓梯的吱咯聲和前門咔噠一聲關上。"
這樣日復一日,他過著這種毫無希望、似乎看不到盡頭的生活。他知道,自己必須做出改變了。
"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等待他的命運之神到來。命運之神不會在南非來到他的身邊,他對自己說,它只會在歐洲的大城市之中。他在倫敦等待了幾乎兩年,受了兩年罪,命運之神沒有來。"
"他心裡明白。除非他促使她來,否則命運之神是不會來找他的。他必須坐下來創作,這是唯一的辦法。"
小說就到這裡結束了。
現實生活中,庫切從IBM公司辭職,離開了英國,到美國攻讀文學博士,從此走上了作家的道路。
(完)